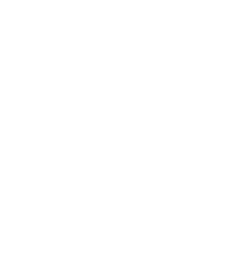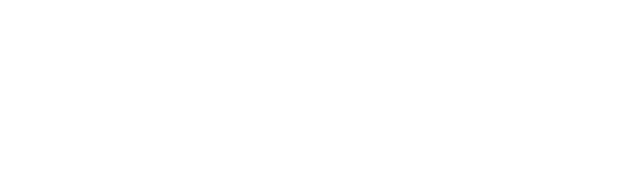“生活的要义,就是满怀兴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睁大你的眼睛,从你遇到的每个人身上看到各种可能性。”这是艾丽丝·门罗在《逃离》那部小说集中给予世人的箴言,也是她的作品想要呈现给读者的要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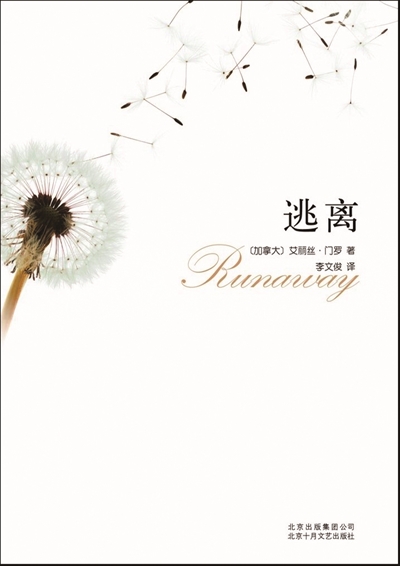
《逃离》艾丽丝·门罗 著 李文俊 译 新经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版

西班牙国宝级导演阿莫多瓦将《逃离》中的三个小说合成一个长篇故事,改编为电影《胡丽叶塔》
当地时间5月13日晚,9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在她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地域,她的出生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离世。她一生共有14部小说集面世,被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2013年,当82岁的她加冕诺贝尔文学奖时,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加拿大人,也是第一位凭借短篇小说折桂的写作者。
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农民家庭的艾丽丝·门罗,几乎一生都在写着有关这一地理背景的人与事。她最初投入写作更像是家庭主妇的逆袭之旅,嫁作人妇的她受困于各种家务,只在夜晚家人入睡后提笔创作,因为难以长时间集中精力,她的小说大多篇幅较短,这也是她后来的创作主要以短篇见长的缘由。这些短篇故事大都发生在身边熟悉的乡镇邻里间,她如实又细致地呈现那一片草木风土之中普通人的情感与生活。过于真实的人物描摹甚至一度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号入座,颇多怨怼。
地理与题材有如画框,限定了故事的体量,大时代的背景似乎也只是若隐若现。但这并不妨碍艾丽丝·门罗在狭仄之中巧妙布局,描绘出人意料的文学图景。即便笔下人物常以女性居多,她作品所展露的广度与深度,依然每每令人叹为观止。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秘书彼得·恩隆德在2013年的颁奖辞中所说,“最宏大的事件藏于人心,最沉重的痛苦隐而不言。一个简短的故事常常跨越数十年,勾勒出人的一生。艾丽丝·门罗在三十页之内呈现的东西,普通作家要用三百页才能说清。她是行文简洁的行家、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在她之前,“短篇小说大师”的称谓只属于契诃夫。

《亲爱的生活》 艾丽丝·门罗 著 姚媛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版
以下是她的写作概况——
1968 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一举获得当年的加拿大总督奖,逐渐确立了门罗在加拿大文坛的地位。之后,门罗的创作进入成熟期。
1976至1990年,门罗先后出版了《你以为你是谁?》、《木星的月亮》、《爱的进程》和《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四部短篇故事集,并两次夺得总督文学奖的桂冠。
20世纪90年代之后,年届六旬的门罗依然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公开的秘密》《好女人的爱》《憎恨、友谊、求爱、爱恋、婚姻》《逃离》《石城远眺》《太多欢乐》和《亲爱的生活》等七部短篇故事集,将加拿大吉勒文学奖和曼布克国际文学奖收入囊中。
2013年,82岁高龄的爱丽丝·门罗迎来她文学生涯中的高光时刻,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颁给了她。
2014年,由她亲自挑选1995年至2014年间成就最高、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传家之物》面世,并于2017年出版中文版。
书比人寿,就让我们在她突破传统的短篇故事里,再度发现那些切中真实生活的图景、情感驿动的瞬间。她所建构的世界实际上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生活的情境就是我们的生活,阅读她,就像是在阅读全部生活。

《传家之物》(加拿大)艾丽丝·门罗 著 李玉瑶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版
“绝望”主妇与自己的“竞赛”
写下诸多女性的不幸与逃离的艾丽丝·门罗,自己的人生故事却过得按部就班,甚至堪称幸运。写作令这位家庭主妇的生活艰辛却斗志昂扬。
十八岁,没有钱也没有机会尝试更多事情的她用奖学金度过了两年大学美好时光,她说那是她这辈子唯一不用做家务的日子。在那里她遇到了第一任丈夫,并在奖学金花光前嫁给了他。那时她20岁,丈夫22岁,他们结婚、搬家、买房、生孩子,还开了一家书店,几年内完成了巨大的人生冒险,很快建立起“非常适当的中产阶级生活”。而年轻的主妇兼书店老板娘门罗从未放弃写作。甚至怀孕期间她会比以往更加疯狂地写,因为她觉得有了孩子,可能就要停止写作了。
她在62岁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谈及过往:“那时每次怀孕都刺激着我要在孩子还没降生之前完成大部头的作品。但实际上,我从没有完成过任何大部头的东西。”一生中她只完成了一部风评不算太好的长篇。
门罗用了15年时间才完成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这部作品记载着她十几年生活的片断。处女作就拿大奖的作家不多,而她足够幸运,出道即巅峰,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的她显然从未想过,另一个巅峰会在46年后她人生的迟暮之年到来。
《快乐影子之舞》面世时她已人到中年,生活依旧按部就班,她在做不完的家务和书店帮忙中间见缝插针地写作,有段时间常写到凌晨一点,六点再起床。这让她感到自己可能会因心脏病发作而死,然而“我想,就算我死了,我也写出了那么多页的东西,他们会明白这个故事如何发展。”她告诉《巴黎评论》,“那是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
除了写作的自律,她也会保持运动的自律——每天走路五公里。“你是在保护自己,这么做会让你觉得如果你遵守所有好的规矩和习惯,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
短篇中写出的长篇“浩瀚”
据说在写《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时,艾丽丝·门罗曾尝试长篇的书写,但最终不得不放弃,她意识到,自己要做的就是把这部小说拆分开,把每一部分写成短篇。而这也让她真正意识到,“我永远写不出真正的长篇小说,因为我无法用写长篇小说的方式来思考。”
作家路内提到他读小说集《传家之物》时的感受:“翻开一看就知道这个作家能够驾驭——如果非要用字数来衡量的话——七八十万字的作品也不成问题。”他把这部短篇集看作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所有的人物互不交叉,故事却发生在同样的地方。“想想奈保尔写的《米格尔街》,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格式。《米格尔街》也是短篇小说集,但我们把它认定为一本‘书’,而不是一个小说集。”在路内看来,门罗具有一种特质,把她某一阶段的作品合起来看,立刻会产生一个长篇小说所具有的体积和容量。
评论家张定浩则以读者的直觉对门罗的短篇做出解析,在他看来,门罗并不注重故事完整性的讲述,故事里几乎看不见高潮到来前的铺垫和浓墨重彩地描摹,甚至正相反,高潮的部分似乎有意被忽略了。
小说集《传家之物》中的第一篇《好女人的爱情》,恰可作为例证。开场对那只收藏于当地博物馆的验光师箱子的铺陈描述,以及早春河岸边三个戏水男孩发现陈尸在水中汽车里验光师尸体的惊悚情节,原本已将故事的悬念拉满,而作家接下来的关注点却并非案情本身,而是如同长镜头的摇臂一般,跟随男孩们从各自的家中一路漫游到镇上的警察局,将整个镇子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尽扫一遍,就连午餐的烹饪细节和公共厕所旁墙上一团刚留下的疙疙瘩瘩的呕吐物都没放过。案件的真相湮没于镇上形色各异的人与他们的日常;背后每个相关者的故事则在类似旁观者的冷静平淡叙述中浮沉。
显然,真正让作家感兴趣的或者说重要的并不是谁是凶手的铺陈与猜测,而是整个镇子,那里人们的生活。“她看起来对什么都感兴趣,甚至说不一定对人,她对所有生活的场景,各种各样的气味,整个感官都是打开的,她教给我们重新去看、去听,这一点特别重要,她不只是抛给我们一个单线的故事。”随意翻开艾丽丝·门罗的一个短篇,都会产生类似张定浩的观感。在这里你看不到故事明确的指向性,她小说中的描写与讲述,甚至人物间的对话,并非为了推进故事情节的开展,而是为了呈现全部生活,“她想尽量抓住生活的整体,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她刻意这么做了。在门罗面前,短篇小说原先的定义失效了。”
模拟生活中的“凭空抓物”
在豆瓣的书友中,有人把艾丽丝·门罗这种避重就轻或者说是“散漫”的写作方式称作“避开风暴眼”的“冷淡风”。它看似简单,却是一种需要花上好几年时间反复打磨才能够掌握的技艺。而对于门罗而言,生活本身即是如此,它并非由一个故事组成,更不能预设其中某一个故事的绝对主导权。而作家所做的就是在虚构的世界里模拟生活的常态,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所言,我们迟早都会在其中一个故事里与自己面对面相遇。
在《传家之物》这部同名短篇小说里,表姑阿尔菲达与“我”以及“我”的父亲之间的微妙关系是作家刻意去描述的,所以对于作家而言,故事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它都隐藏在人们的言语和对彼此的情感、态度之中了。在这篇小说的最后,门罗描写了“我”离开阿尔菲达家之后内心泛起的波澜,它成为豆瓣读者笔记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段落——
“我走了一个多小时,看见有一家杂货店开着。我进去喝了杯咖啡。咖啡是重新加热的,清咖,很苦——味道像药一样,正是我想要的。我已经感到轻松,现在更是开始感到快乐。多么快乐啊,像这样独处;像这样看着午后灼热的阳光照在屋外的人行道上,有一棵树的枝条刚开始长出叶子,投下斑驳的树影;像这样听着商店里屋传来的球赛的声音,刚才为我上咖啡的男人正在听收音机。我没去想我将要写的关于阿尔菲达的故事——没有特地去想这个——而是想到了我要做的工作,更像是凭空抓物,而不是架构故事。人声的鼎沸如同沉重的心跳般传了过来,充满哀伤。这阵阵动听的一本正经的声波,蕴含着冷漠的、几乎不近人情的赞许和悲叹。……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觉得我必须关注的,这就是我希望自己的生活呈现的模样。”这是小说中的“我”在那个瞬间的生命感触,这个“我”用更全面的视角去看待过去家族的一切。“我”开始独立于原生家庭,不被牵拖和抑制,接受无法避免的阴影,理解人性的复杂与闪光……“我”获得了小说中的“传家之物”,我们每个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某个瞬间可能会具有如同“我”的感同身受。
而同时,“我”也成为作家艾丽丝·门罗的替身,说出她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像是凭空抓物,而不是架构故事”。如她曾经所言:“小说不像一条道路,它更像一座房子。你走进里面,待一小会儿,这边走走,那边转转,观察房间和走廊间的关联,然后再望向窗外,看看从这个角度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她书写生活的方式,也正是生活本身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模样。
《巴黎评论》与门罗的对谈(节选)
女性也可以写奇特的边缘化的东西
问:你用笔记本记录吗?
答:我有一大堆笔记本,上面的字迹非常潦草,就是把任何冒出来的想法记录下来。我看着那些草稿常常感到疑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是否有任何的意义。我与那些有天赋的作家相反,你明白,我指的是那种文思泉涌的作家。我不是一下子就能把握住它——我是指我希望表达的东西。我总是误入歧途,然后再把自己拽回来。
问:你如何意识到你写的东西误入歧途了呢?
答:我会沿错误的方向写上一整天,还觉得,嗯,今天写得不错,比平时写的页数要多。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意识到我不想继续写那篇东西了。当我感到对于自己所写的东西特别犹豫,需要强迫自己才能继续写下去的时候,我大概就明白我写的东西有很大的问题。经常是在写到四分之三的时候,我就会到达某个临界点,相对还算早,就觉着要放弃这篇东西了。之后,会有一两天,我非常沮丧,到处抱怨。我开始想些别的可以写的题材。这就像是一场外遇:你和新的男子外出约会,只是为了从内心的失望和折磨中走出来,你其实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可是你还没有注意到。不过,对于那篇我想放弃的故事,会忽然有些新想法从我脑子里冒出来,我又明白该如何继续下去了。可是,这些想法似乎只有在我说完“不行,这行不通,算了吧”之类的话之后才会出现。
问: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吗?是否有作品对你产生过影响?
答:三十岁之前,阅读真的就是我的生活。我就活在书里面。美国南方的作家是最早一批让我感动的作家,他们向我证明你可以描述小镇,描述乡下人,而这些正是我非常熟悉的生活。不过,有意思的是,连我自己都没太意识到,我真正热爱的美国南方小说家都是女性。我不是太喜欢福克纳。我热爱尤多拉·韦尔蒂、弗兰纳里·奥康纳、凯瑟琳·安·波特,还有卡森·麦卡勒斯。她们让我觉得女性也可以写奇特的边缘化的东西。
问:这也是你一直在写的东西。
答:是的。我逐渐认识到这是女人的领域,而关于现实生活主流的大部头小说是男性的领域。我不知道这种边缘人的感觉是怎么来的,我并没有被排挤到边缘。或许是因为我自己是在边缘社会长大的。我明白,伟大作家身上的某些东西,我感到自己是不具备的,不过,我不确定那究竟是些什么。我第一次读到D.H.劳伦斯的作品的时候,觉得极度不安。我总是对作家有关女人性方面的描述感到不安。
问:你能告诉我究竟是什么让你觉得不安?
答:我的不安是,当我成为其他作家的描述对象的时候,我怎么能是一名作家?
问:你写作的自信心如何?经过这么多年,在自信心上有什么变化?
答:对于写作,我一向是非常自信的,但这其中又夹杂着担心,担心这种自信是完全错误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的自信源自我的愚钝。还因为,我离文学的主流那么远,我没有意识到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容易成为一名作家,对较低社会阶层的人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在那里,你连个真正读书的人都遇不到,而你自认为还写得不错,你当然觉得自己确实有罕见的天赋。
问:在避开与文学界的接触方面,你可称得上是个高手了。你是有意识地这样做,还是特定的环境使然?
答:有好长一段时间,这当然是环境使然;不过,后来,就是一种选择了。我想我是个友善的人,但不好交际。主要也是因为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母亲,我需要留出大量的时间,而这被解读成害怕交际。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已经丧失了自信。我会听到太多我不理解的谈话。
问:所以你对于置身主流之外感到高兴?
答:这可能正是我想说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无法作为一个作家很好地幸存下来。在一群比我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人当中,我很可能会失去自信。他们经常高谈阔论,而且在信心方面都公认比我更有底气。不过,话说回来,对作家,这也很难说——谁是自信的呢。
问:你用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故事,会休息一阵子吗?
答:我几乎是马上就开始下一个故事的写作。有可能停止写作这个想法让我有点惊慌——就好像一旦停下来,我可能会永远停止写作。我脑子里可是储存了一堆的故事。不过,写作不仅需要你有个故事,也不仅仅是技能或是技巧,还需要有一种激情和信念,没有它,我无法写下去。上了年纪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你的兴致有可能被耗尽了,你无法预见这一点。它甚至在一些曾经对生活充满兴致和责任的人身上也会出现,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你在旅行的时候,可以从许多人的脸上看到这一点——比如,餐馆里的中年人,或者像我这样在中年的尾巴上、即将步入老年的人。你能看到这一点,或是像只蜗牛一样感觉到它,那种眼神里的讪笑。那种感觉就是,某种程度上,人对事情做出反应的能力被关闭了。我感觉这就像是你有可能得关节炎,所以你要锻炼,以防止自己患上这种病。我现在更加意识到,所有东西都会有失去的可能,包括以前填满你生活的那些东西。或许,应该坚持下去,做些什么来避免它发生。失去这种激情和信念可能才是危险所在。这可能是一头野兽,藏身于老年人心理的最深处——你对于值得做的事情也失去了感觉。(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原载《巴黎评论》第131期,1994年夏季号)
责任编辑:李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