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应以怎样的方式与态度理解“他者”——
与一位十八世纪“世界公民”的精神共振
设想一位生活在18世纪、热衷品评、比较中西时事见闻,兼有写信分享欲的中国哲人游历欧洲,在他写给亲友的123封信中毫不避讳地讽喻西方风俗世态,比照东方道德哲思、人情伦理——结果不但没有被他所嘲讽的西方人士厌弃,反而大受欢迎……在英国18世纪中期重要作家哥尔斯密的书信体散文集《世界公民》中,主人公李安济,就是这位擅长“碎碎念”的中国哲人,一位来自中国河南的幸运的“世界公民”。

18世纪的“中国热”中,西方艺术家弗朗索瓦·布歇关于中国的想象图景。
2024年,《世界公民:中国哲人信札》的中译本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世纪欧亚文学交流互鉴研究”子课题“长18世纪欧洲涉东方题材文学目录汇编和精选译注”出版书目中的一部正式面世。比之同时代写下《格列佛游记》的斯威夫特、《汤姆·琼斯》的作者菲尔丁,哥尔斯密算是“冷门”,而从这些充满机敏幽默和温和讽刺的信件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作家“精致的松弛感”,更重要的是,他所传递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普世认知与态度——我们的世界并非从东西对立中产生,而是源于多种差异性、知识、认识与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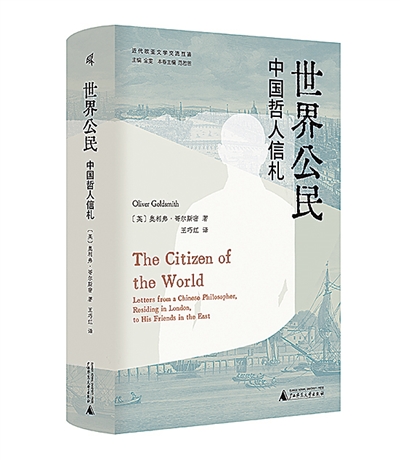
《世界公民:中国哲人信札》
(英)奥利弗·哥尔斯密 著
王巧红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10
今天我们如何解读这一“于文学虚构中重构了18世纪全球化浪潮下的思想碰撞”的意义丰富的文本?又应以怎样的方式与态度理解世界和“他者”?《青岛日报》就此专访本书的译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业博士王巧红。答案或许就隐藏在读者与本书主人公、18世纪“世界公民”李安济,以及他的创造者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理想的精神共振中。
文类模糊的多面向书写
“外来者”的城市探索,是作家展开社会批判的有效载体
青报读书:后记中说,您在读博时通读了英国18世纪作家奥利弗·哥尔斯密的五卷本全集,其中最爱的是这本书信体散文集《世界公民》,作品最吸引您的部分是什么?
王巧红: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第二年,选定英国18世纪中期作家奥利弗·哥尔斯密为主要研究对象。之后我系统研读了由英国学者、哥尔斯密研究专家亚瑟·弗里德曼1966年主编的《奥利弗·哥尔斯密全集》,第二卷即《世界公民:中国哲人信札》。第一遍阅读期间,我尤其关注哥尔斯密早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其中重要的一部即《世界公民》。
这部作品最初吸引我的有两点:一是“温和的讽刺”,例如,作者描写英国文学界的状况,“在这个想象的共和国里,每个成员都渴望掌权,却没一个人愿意服从。每个人都把同伴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同道中人。他们互相诽谤,互相伤害,互相蔑视,互相嘲弄”;二是哲思的话语,例如,主人公李安济劝慰屡遭挫折的儿子,“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不幸,你必须学会忍受。爱情失意,是青年的不幸;壮志难酬,是中年的不幸;未果的贪婪,是老年的不幸。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三者都会向我们袭来,我们有责任保持警惕。”
进一步的阅读和研究让我看到《世界公民》更多的面向。第一,文类的模糊性。文类在18世纪是不确定的,我们现在对文类的区分,依据的主要是浪漫主义之后的标准。若从虚构了故事框架与人物,并假托某一契机或身份以表达政治见解、文化立场或启蒙观念等角度视之,称《世界公民》为书信体小说亦未不可。若以《帕美拉》、《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来衡量,则确实区别较大。哥尔斯密仅借一种受众较广的通俗形式以传达见解,这也是启蒙时代的一种文学传统。若称“散文”甚或“游记”,亦有其道理。
第二是城市漫游者的前现代书写。这部作品中呈现了体裁模糊、现代的时间观、现代化的主人公以及现代的读者群体等文学现代化特征,这些既是哥尔斯密继承与发展欧洲东方信札传统的结果,也是这一文类传统在18世纪中期英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自然演变的结果。书中对伦敦街景的碎片化速写——从街头妓女到贵族的马车,从咖啡馆到街头修鞋匠——构成了现代都市书写的先声。这种“外来者”的城市探索,是作家展开社会批判的有效载体,也是间接参与社会热点话题的媒介。哥尔斯密借此展开有争议话题的社会批评和讽刺,是表达其英裔爱尔兰人身份的独特方式。
《世界公民》常读常新。在当代,它让不同文明在想象的对话中彼此照亮,这种开放性的智慧在当今文明冲突频发的时代,显现出超越时空的预言性质。
异于传统的东方主人公形象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东西方文化的互动呈现一种独特的“镜像共生”关系
青报读书:在18世纪西方的主流话语体系里,遥远的东方文明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世界公民》中的李安济形象,如哥尔斯密在前言里的描述:“简洁”“简朴”“庄重”“爱说教”“沉闷”……这些所反映的是当时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知识分子的典型印象吗?
王巧红:在18世纪的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中,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的形象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矛盾性,而哥尔斯密在《世界公民》中塑造的李安济形象,恰恰是这种矛盾性的集中体现。西方的中国形象本身源自于西方与中国文化的碰撞、混杂,是西方现代性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哥尔斯密选择借用东方故事中常见的传统元素和叙事主题,并对之做了现代化的处理。相比于传统东方故事中的中国主人公,李安济·阿尔坦济身上的中国特性并不明显,他不携带鸦片或烟草,不使用筷子,不吃“熊掌或燕窝”,说话也完全没有东方式的风格,甚至他的面容也没有“真正的中国人的样子”。哥尔斯密没有特别地描述中国哲人李安济的中国特性,只交代他来自中国河南,曾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他的形象并不符合当时英国大众心目中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人的形象。就此,伦敦18世纪的评论杂志《每月评论》在《世界公民》出版后指出,作品中主人公的亚洲特征不够明显。换言之,《世界公民》中的中国人李安济的形象既不符合这一时期欧洲流行的游记和报告中流行的中国人的形象,也不符合东方故事作品中对中国人形象的集体刻画。尽管他有时表现得不太具有中国特性,但其中国哲人的身份还是为他提供了一个超凡的视角去观察英国的风俗习惯和文化。
作家个体的见解、趣味、价值观念等是社会集体生成的,作家个体从周围环境中获得写作材料、观点,其作品又是社会动态变化的回响。哥尔斯密对东方(中国)的认知水平是当时欧洲知识界的普遍水平,其知识来源为知识界流传的有关东方的畅销作品。“李安济”一名或出自霍勒斯·沃波尔的短篇讽刺作品《旅居伦敦的中国哲人叔和致北京友人李安济书》。
另外,《世界公民》中的“中国哲人”和“黑衣人”代表两种并行的文化,他们一起结伴在伦敦旅行时,“黑衣人”提醒“中国哲人”看到表象之下的文化体系,避免用极端理想化的或有偏见的方式看待文化差异。在《世界公民》的结尾,他们最终相约一起到各地旅行继续做“流浪的哲人”,同时结尾处“中国哲人”的儿子和“黑衣人”的侄女结婚的情节安排也是为了加强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纽带,预示着两种文化的融合,展示了一种跨文化的对话。然而,从商业出版的现实因素考虑,或许也是作者为了将来能根据读者的反馈情况为写续集留下的余地。
青报读书:《世界公民》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哥尔斯密对于东方思想文化的一种对等与互鉴的态度,书中总是借东方哲人——主人公李安济之口反讽伦敦的诸多文化陋习。在范若恩教授的序言中,我们也看到一种后世西方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即:认为在启蒙思想兴起的18世纪,东方文明作为一种他者的文明,并不仅仅以西方的对立面或者器物层面的风尚存在,而是其学习借鉴的对象和反思构建自我的一种方式。您个人如何理解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之间这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王巧红:“两希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通常被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两个重要源头。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东西方文化的互动则呈现了一种独特的“镜像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文化挪用或单向影响,而是一种通过他者视角重构自我的动态过程。东方文明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第三个源头。
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文本:李安济作为虚构的中国哲人,实则是一面被欧洲启蒙知识分子刻意打磨的棱镜——既折射出伦敦社会的文化矛盾,又将东方思想转化为批判理性的载体。《世界公民》采用的书信体与嵌套叙事,本质上是“文化间性”的文学具象化。李安济的“外在视角”与英国收信人的“内在视角”形成复调对话,这种叙事张力映射出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认知困境:既要借助他者解构传统权威,又难以彻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
金雯教授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成为18世纪欧洲的一面魔镜,为早期现代的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其中反观自身文化的参照系,时而显示相似性,时而显示相异性,凸显了东西方文化之间同异相杂的复杂关系。这种复杂互动启示我们,文明互鉴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交换,而是在权力网络中进行的意义再生产。18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互动关系说明,当文化差异被转化为反思性资源而非等级化标签时,异质文明间能激发出超越本土局限的思想潜能。当前全球现代性危机中,重审这段历史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二次启蒙”的路径——不是寻找普世答案,而是培养容纳多重真理的阐释弹性。
兼具思想与流行的跨文化书写典范
作家是表达时代精神的唇舌,也被时代造就
青报读书:最初在报纸上连载的《世界公民》,是一部两百多年前欧洲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作品,那么作家写作的初衷是什么?是迎合读者对于东方思想文化、人情世故猎奇的阅读趣味,还是如当时的诸多启蒙者那样,立意在以他者的视角,对于西方世界的陈规陋习给予反讽和革新?
王巧红:作为一部以虚构的“中国哲人”视角观察英国社会的书信体作品,《世界公民》的创作初衷既与18世纪欧洲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也与哥尔斯密个人文学理想和现实生存处境不无关系。
第一,作家是表达时代精神的唇舌,同时也被时代造就。18世纪的欧洲正经历“中国热”,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对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充满理想化想象,将其视为道德典范或哲学乌托邦。哥尔斯密以“中国哲人”为主角,模仿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用书信体呈现异域视角,确实能满足18世纪读者对东方的好奇心,满足公众对遥远国度的浪漫化想象。同时,哥尔斯密的真正目标并非单纯猎奇,他借用一种理想化的中国事物来反衬英国或欧洲的事物,借此提出自己的感想或评论,其根本用意在于更好地发展本国的文化。哥尔斯密描写东方(中国),其目的在于启蒙或讽刺英格兰,而不在于更多地理解中国。整体上,哥尔斯密对中国文化没有热情,他的态度是淡漠的,而不是对抗的或敌对的。18世纪英国社会生活中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并不同样地反映在文学中,反而在文学中经常出现反对和批评“中国热”的声音。英国18世纪文学整体上充满了对欧洲流行的中国风尚的负面评价。作为一名职业报刊作家,哥尔斯密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文学趋向,学者闫梦梦指出,哥尔斯密“反对物质上的中国风,同时又实践着一种文学意义上的‘中国风’”。
第二,作为英国18世纪中期的作家,哥尔斯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一位游历欧洲、经济拮据的文人,哥尔斯密对社会不公和人性弱点有深刻体察。他见证了商业出版和职业作家的兴起和英国社会的激烈变动,英法七年战争、英国海外殖民地扩张等构成了哥尔斯密写作的背景和底色。作为18世纪英国商业出版大潮中的一名职业文人,哥尔斯密在为了商业利益而写作之外,更是一位善于洞察社会现状、思考人类命运的严肃作家。信札作品不仅是哥尔斯密为了迎合大众读者阅读需求和流行文化,而且是他以“世界公民”理想对抗英国殖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一次尝试。
第三,哥尔斯密借助外来者和旅行者展开社会批评和讽刺,也找到了新的表达其英裔爱尔兰人身份的方式,帮助他回避有争议的话题。
总之,《世界公民》形式上利用了读者对异域文化的猎奇心理,但其核心意图在于通过幽默反讽促使英国社会自我反思,呼应了启蒙时代“理性审视传统”的精神。这种策略既保障了作品的通俗可读性,又实现了思想深度,使其成为18世纪欧洲跨文化书写的典范。
青报读书:如您所言,相较于同时代的作家斯威夫特、菲尔丁和约翰逊,有关哥尔斯密的研究算是“冷门”,这主要是源于他职业报刊作家的身份吗?《世界公民》是否可以看作他无心插柳的成功。
王巧红:哥尔斯密作为职业报刊作家的身份本身并非导致其“冷门”的唯一原因,其古怪多变的性格,为人和为文上的矛盾性,权威作品全集出版较晚等因素也导致其遭受冷遇。
关于哥尔斯密的职业报刊作家身份,我认为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哥尔斯密对职业报刊作家(职业文人)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他一方面谴责伦敦出版的机械化和粗俗化倾向,渴望回到传统的赞助人制度,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书商和阅读大众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新的赞助人。他处在追求文学声望和依靠报刊写作快速获利之间的两难选择之中。第二,哥尔斯密的报刊写作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艾迪生式高雅的报刊散文传统、伦敦快速发展的出版业和报刊业、党派论争、报刊之间的激烈竞争、报刊为反对贵族文学趣味而做的共同努力以及哥尔斯密的爱尔兰人身份等多重因素共同形成一种合力,使得哥尔斯密的诗学和报刊写作之间充满张力。这种张力既是文学标准和职业写作要求的差异所致,也是18世纪文化和科技领域发展不同步的结果。
哥尔斯密发表《中国人信札》好像是一个偶然事件,其实不然。《世界公民》在创作之前经过一段相当长的酝酿过程,他在写作《中国人信札》之前,土耳其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都曾引起他的兴趣。哥尔斯密最终选用一个中国人是因为“中国人能提供更多的新鲜感”,这说明他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顾及大众读者阅读趣味的结果。此外,还有另一个现实因素是,英国具有大量便捷的有关中国信息的参考资源,主要包括法国耶稣会士柏应理用拉丁语翻译的《大学》、《中庸》和《论语》等中国典籍,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以及杜赫德的《中国通志》等,它们都是当时欧洲流行的有关中国的基本参考材料。
精致的松弛感中暗藏的锋刃
如何用文学形式处理宏大历史命题——不是通过说教,而是经由形式创新将历史张力转化为审美张力
青报读书:您提到作家同时代的另一位职业报刊作家威廉·赖德,曾经评价《世界公民》这本书“闲适又精致”。这种赞美,感觉类似于我们今天经常讲的“一种精致的松弛感”,或者今天我们的阅读趣味与200多年前的西方普通大众读者也并没有太大的反差?单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您如何来评价它所具有的文学价值?
王巧红:这个问题非常敏锐,触及了文学经典与当代审美之间的奇妙共振。书中那些看似闲适的咖啡馆絮语、市集见闻,实则暗藏锋刃。研究者西默斯·迪恩曾敏锐地指出哥尔斯密作品中表面的宁静下潜藏的隐形的危机感。“危机感在他奇妙的、多变的、宁静的散文结构和语气中显得如此遥远”,但其作品表面上创作的轻松并不能掩盖这些作品中的不连贯性。
这部作品的永恒魅力,或许正在于它完美平衡了消遣与沉思、异域与本土、讽刺与悲悯。当我们将“精致的松弛感”投射到18世纪文本时,不应忘记:真正的文学经典从来不是时代风潮的应声虫,而是能穿越时空,不断重构解读可能性的智慧晶体。
正如作家赵松老师指出,两百多年过去了,我们阅读这本书时仍觉得它有意思,大家在书中能找到什么?应该是“智慧和趣味”。时间、历史不断延展,却没有消除人性的弱点。哥尔斯密对于人和人性的观察和思考并不过时。
青报读书:在您看来,《世界公民》的历史价值是否更大于其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它对于今天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的文学创作又有哪些启示和意义?
王巧红:作为译者,我认为这部作品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一种互文共生的关系。它在文学虚构中重构了18世纪全球化浪潮下的思想碰撞,其历史意义恰是通过文学性的叙事策略实现的。
作品的文学性恰恰是其历史批判的载体。采用书信体与游记体杂糅的叙事形式,模仿了18世纪欧洲常见的知识传播媒介,却在文体拼贴中暴露出启蒙理性的裂缝。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大量出现的误读与误译情节,构成精妙的元叙事装置。这些文学策略不仅制造喜剧效果,更隐喻着跨文化交往中永远存在的阐释鸿沟——这种后现代式的自觉,使作品超越了其时代局限。这部18世纪作品示范了如何用文学形式处理宏大历史命题——不是通过说教,而是经由形式创新将历史张力转化为审美张力。在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全球文化生产的今天,这种将技术变革、文化碰撞与人性探索熔于一炉的创作范式,或者值得当代作家镜鉴。
启蒙语境下的“世界公民”理念
哥尔斯密反对不加反思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提出把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世界主义者
青报读书:在第108封信里,哥尔斯密借李安济之口提出:如果每个国家的有用知识,无论这个国家多么野蛮,都被明智的观察者收集起来,那么其好处将是不可估量的。他还为“明智的观察者”做了描摹:他“既不因骄傲而自满,也不因偏见而僵化;既不拘泥于某一特定体系,也不只精通一门特定科学;既不完全是一个植物学家,也不完全是一个古董商。他的头脑中应当掺杂着各种知识,举止应当因与人交往而变得人性化……”是不是可以把这些特征理解为一个18世纪作家对于真正的“世界公民”的定义?
王巧红:是的,哥尔斯密在此处描写的“理想的旅行者”、“明智的观察者”可以视为18世纪“世界公民”的早期定义或理想化想象。在《世界公民》中,哥尔斯密暗示若要公正、准确地评估英国社会,就需要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态度。他反对带有偏见的民族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广泛的统一体,所有的民族带着自身的、从先天环境中带来的优势和劣势,在各自不同的人文环境中生存,是一个共同的文化体,这是18世纪启蒙者的一个普遍认知。“世界公民”是不局限于狭隘的关切,作为不同地方的风俗与成就的旅行家和观察者,不受狭隘的影响,蔑视地方小团体的琐屑。
哥尔斯密在《世界公民》中描述一位英国人给法国战俘的捐款附言中写道:“一个英国人,一个世界公民的微薄之力, 献给赤身裸体的法国战俘。”哥尔斯密反对不加反思的、狭隘的爱国主义。其数篇散文、诗歌作品,都提出把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世界主义者。然而,哥尔斯密的这种对理想旅行者和终极世界主义者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是自我陶醉式的。他的职业作家身份使其所宣称的世界公民思想、成为一名世界公民的愿望变得更复杂。他有时颂扬欠发达民族的文化潜力,有时又鄙视他们不文雅,这些表述交替出现,体现了他态度上的矛盾性。
总之,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理念是其在启蒙语境下的特殊表达:它既是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工具,也是知识精英重构全球认知秩序的蓝图。尽管受时代局限未能完全摆脱欧洲中心论和阶级偏见,但其对开放性、多元性、人文性的强调,仍为当代讨论跨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历史参照。(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青岛日报2025年2月23日4版
责任编辑:岳文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