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潜藏女神般灿烂的光芒,是一种重要的力量
——每一位女性都是一个阿佛洛狄忒
“唯有你,是宇宙的指引之力,没有你,万物便无法涌现于灿烂的阳光之下,在喜悦与美好中生长……”古老的《荷马颂歌:致阿佛洛狄忒》中,女神阿佛洛狄忒光芒四射,承载着欢愉美好的能量。但这只是表象,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这位女神的形象始终处于被一再定义的张力中。
她是爱与欲望的化身,是生育与丰饶之母,亦是罗马神话里的维纳斯,是关于美的范式,也是抗争与解放的符号;而所有耀眼的光芒周围都会有阴影盘踞,她也是希腊人定义的“搅动一切的女神”,代表对女性和非传统性取向的恐惧与迷恋,以及性与暴力之间长久而危险的关系,希腊神话中,她与战神阿瑞斯的私情孕育了“得摩斯(恐惧)”和“福波斯(恐慌)”,却也造就了“哈耳摩尼亚(和谐)”……
在当代语境中,恰是这位“混合之神”的多重性,揭示了女性经验在历史命运中的复杂与丰盛。
英国历史学家、作家贝塔妮·休斯在《维纳斯与阿佛洛狄忒:一个女神的历史》中赋予了这位爱与欲望之神升华的人性意义:“欲望是对美的追求——无论‘美’可能意味着什么。欲望让我们对世界产生美好的感觉,因此也让我们在世界中变得伟大。它是激励我们行动、存在、思考的生命力,爱的意义不在于满足,而在于共生;人性的意义在于滋养智慧以及人际关系中——无论是身体、智力、社交还是文明层面——日益增长的喜悦。”从这层意义上说,阿佛洛狄忒“不仅是我们低俗时刻的催化剂,更是我们最高尚时刻的推动者。她不仅是激情的载体,更是哲学的媒介,是我们可以用来思考,也可以用来感受的共鸣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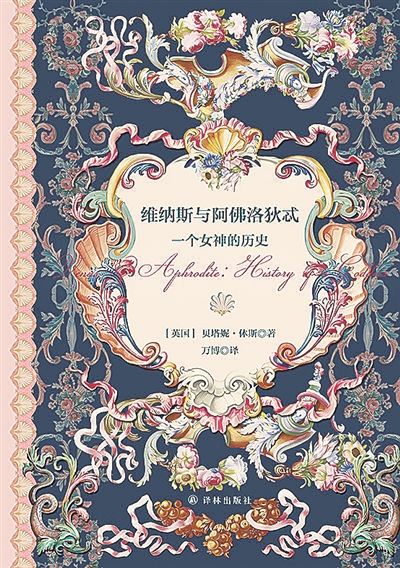
《维纳斯与阿佛洛狄忒:一个女神的历史》
(英)贝塔妮·休斯 著
万博 译
译林出版社2025.02
我们将每年的3月8日都戏称为“女神节”,是因为每一位女性,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阿佛洛狄忒,她或许是一切混乱、麻烦、变幻莫测和生机勃勃之事的制造者,因为她们身上潜藏着女神般灿烂的光芒,而更易被现实和命运的阴翳遮蔽,但她们绝不是只有“原始、片面、一心一意的野心或激情”的神祇,而是一种重要的力量,提醒我们,当我们将这些激情强加于他人和周围世界时会发生什么,于是又担当起指引我们穿越混乱的向导。
如果想要对这个世界有更加深入且透彻的觉察与体验,你须选择以某一个阿佛洛狄忒的视角介入,她们会向你描摹诸如成长的创痛,人到中年的脆弱、犹疑,关于爱、失落、流离的情境,某种亲密关系的悖论,难堪却依然试图找到的关于自我或他人存在的真相……生命中所有易被忽略的意义重大的瞬间,那些看似微不足道情境背后的惊涛骇浪与地动山摇,是她们各自用独特光芒照亮的世界的一面。如贝塔妮·休斯所言“她们自己既是伤口,也是绷带”,因此最清楚这个世界何以残酷又何以美丽。现在,一起来倾听她们讲述的故事。
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是什么
身体的探索、同学间的霸凌、对年长异性的爱慕、隐秘的家庭生活、亲人的离去、友谊的背叛、自我的弃绝……爱尔兰女性作家、BBC英国短篇小说奖得主露西·考德威尔在她的首部短篇小说集《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中铺陈了成长中的混沌时刻。
当世界猝不及防地揭开面纱,我们将如何从成长中幸存?是否相信了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我们便能从这个残酷的世界脱困?
在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里,考德威尔真实而又细腻地记述了一位女性初为人母的历程和复杂感受,欣喜伴随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慌乱,而在与新生命对视的那一刻,她已变得笃定。“我们告诉他,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那个廉价的袖珍收音机正在谈论加沙、埃博拉、紫杉树行动,还有全球变暖,我们看着彼此,就像数十年来、数百年来父母们一定会向新生儿们娓娓道来的那样告诉他,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是他的工作。到了某个时刻我们不再给出理由,只是告诉他,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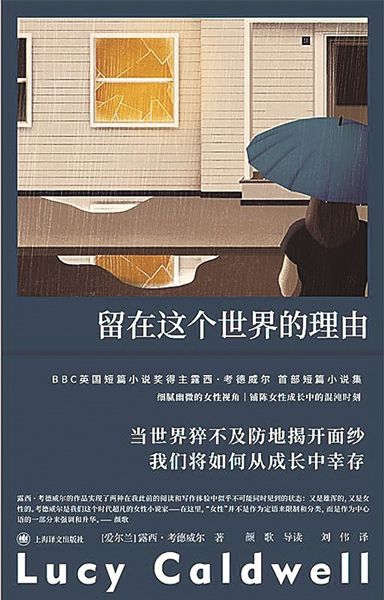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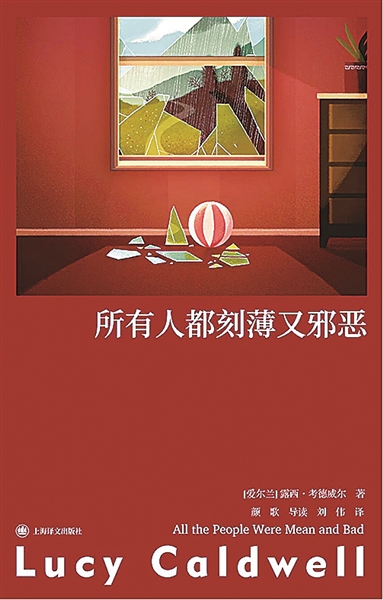
《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
《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
(爱尔兰)露西·考德威尔 著
刘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01
没有谁能像考德威尔这样,将初为人母的情绪捕捉到每一个脉搏,在另一部短篇小说集《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中,作家继续放大读者的感官,《奉献》中的母亲也在凝视刚出生的孩子:“柏拉图和他的洞穴,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和他的一杯毒芹。你花了数年研究他们,试着把自己塑造得像他们那样思考。近来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至少变得无关紧要。现在你想知道他们是否凝视过一张新生儿的脸,感受世界的倾斜和消逝;是否见证过一个孩子长大,感受时间造成的恐慌”;《如此这般》里,误以为丢失了孩子的年轻母亲思绪飞扬:未来关于孩子的记忆会消失不见,婚姻因为内疚和焦虑无法继续,丈夫争夺儿子的抚养权,而儿子完全不记得他曾有过一个妹妹……虚惊一场后她仿佛“一个流浪者造访了另一个世界,并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但回到自己的世界后,却发现时间连一分钟都没有过去。”
考德威尔告诉我们,女性们常常以未成年的心态被推入成人世界,她们需要时间和契机成长,而这一过程中,她们也常常步伐踉跄,滑入成长的漩涡。在《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这部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里,女主人公经历了一趟可能改变其人生轨迹的夜间航班,遇到了带来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一个人,她与他探讨了是否相信“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的命题。结局很平淡,叙述风格同样内敛,而这也正是考德威尔试图传达给我们的生活真谛,或者说是试图传达给成长中的女性的真相——所有你将去往的地方,所有朦胧不清的未来,所有你将亲历的词语,你将爱上的人……在时间的河流里,如潮水般涌来又退去,而你的灵魂会以某种方式记取,“一切都是永恒,没有什么会失去”,或许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即是经历一切,并在成长中学会与一切和解。
小说中经常使用的第二人称叙事,据说也是目前西方写作的一种流行风尚,初读时仿佛过于亲昵了些,而这正是作家的用意,将读者迅速拉入主人公所处的情境,那些中文语境里鲜少探讨的成长的幽暗时刻,在她幽微平静,甚至可以说是不动声色的第二人称表达里反而具有了某种戏剧性的张力。
“不立意于表达反抗,也并非希望来达成申诉”,为这两本小说集写下导读的作家颜歌感受到了作者冷静铺展下的宏大女性力量。她说:考德威尔平静、幽微、多样的叙事表达就是宏大的力量本身,她的角色如水般存在着,或在深井中,或在激流里,她用节制而充满张力的语言描绘她们的存在。考德威尔自己也说过:“我们要对词语的力量保持警惕,最重要的是,要警惕它们的幽灵——也就是你用它们来表示什么或不表示什么的方式,或者避免把它们直接说出来的方式。”她说,我们应该闭着眼睛来获取信息,这样才能听得更清楚。
如果听得足够细致入微,你就会在考德威尔的短篇中发现更多并未讲出和描述的东西,包括城市、国家、宗教、战争、历史、政治,以及不自知的内心,所有矛盾、挣扎、和解和凝视。正像爱尔兰作家凯文·鲍尔所说:没有人可以在一篇短篇小说里融入比露西·考德威尔更多的东西,也没有人可以比她看起来做得更少。
如何对你爱的人说你爱他们
在小说集《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的最后一个短篇《亲密》中,作家考德威尔虚拟了一位母亲写给幼子的信,信中罗列了七件母亲叮嘱孩子重要的事。其中最后一件事,被这位母亲,也就是作家称作“最平庸也最深刻的一件”,那就是“对你爱的人说你爱他们”。她说:“到头来,这将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唯一可以带走的东西。现在就说出来吧。这些小小的、琐碎的、能带来改变的言辞。
这仿佛是为美国非虚构文学大师薇薇安·戈尔尼克的回忆录《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所做的注脚。在这部首次引入中文版的作品中,戈尔尼克记述了人到中年的自己与母亲之间爱恨交织的“战争”。“你为什么还不走?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这无情的质问中隐含的是对这位与自己最亲密的女性最真实的爱:“两个有着相似局限的女人,她们紧密联结,只因一辈子都生活在对方的轨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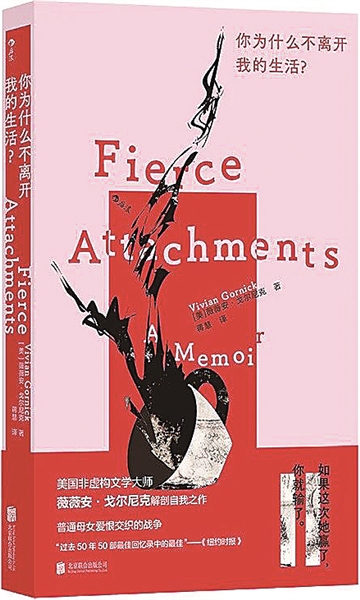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
(美)薇薇安·戈尔尼克 著
蒋慧 译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02
戈尔尼克只身潜入自我深处,不仅尖锐地审视母亲,也解剖自己,不加掩饰地袒露对母亲的复杂感情。“我跟母亲的关系并不好,年岁越长,往往像是越糟糕”;“我无比渴望远离她,却没法走出她身处的房间。我害怕她下班回家,但她归来的那刻我却从未缺席”;“我想把心中迸发的光芒分一点给她,把自己生活里的巨大快乐匀一些给她。只因她是与我相识最久的亲密伙伴”。
“我是我母亲的女儿,我为什么想要远离她?我又怎么可能真正远离她?”在戈尔尼克眼中,母亲永远是那个擅长扫兴、放不开对子女干预的人,也是那个自我矛盾丛生的人——
“她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只能把所有消极情绪都化作自怜和愤怒,她习惯用愤怒掩饰恐惧和惭愧。她热情而尖刻、失控而慷慨、讽刺而挑剔,有时,还会展现她所理解的深情:她在满心洋溢着自己最害怕的柔情时,呈现出那种粗暴而强横的做派”;
“这就是她的处境:在这个厨房里,她有自知之明;在这个厨房里,她烦躁且无聊;在这个厨房里,她把家务干得无可挑剔;在这个厨房里,她鄙夷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对自己所说的‘女性生活的空虚’深感恼火,又在分析小巷里的复杂情势时放声大笑——那笑声我至今都还记得。早上消极,下午叛逆,她每天被创造,也被毁灭。她如饥似渴地抓住自己唯一能够得到的东西,并渐渐爱上自己的勃勃生机,然后,她又感觉自己简直像个叛徒”;
“我在旁人眼中:念研究生,写文章,出书,结婚又离婚,一生无子女,‘新女性、自由女性和怪女人’。但在母女关系中:我始终是那个没能实现母亲期待的普通女儿。普通女儿无法达成母亲亘古不变的期待,母亲也并不想找寻那个云遮雾绕的自我。一直以来,我用尽各种办法,试图摆脱母亲的影响,避免成为母亲的翻版。我曾把母亲当作自我与自由的对立面,可母亲其实不是任何概念的反义词”。
这部被《纽约时报》称作“过去50年50部最佳回忆录中的最佳”的作品,也得到同行的力荐,美国作家、国家图书奖获得者乔纳森·勒瑟姆称戈尔尼克为一位绝顶高手,“将场景与对话写得十分精练,将包袱藏得很深,留白也用得恰到好处,她这种控制力让我至今仍在思考,为何她从未涉足小说。”或许只有用非虚构的方式讲述,才能让那些深埋的爱与情感得到最真实的袒露与爆发。
对于亲情的回忆性书写成为2025年开年女性书写中的一个重要题材。与戈尔尼克相比,作家皮皮表达爱的方式则更具有中国式家庭关系的传统气质。最新面世的亲情散文集《拉着你的手从黑夜一直走到春天》中,皮皮在其中写母亲、父亲和舅舅。皮皮的妈妈有电影《好东西》女主的气质,是一个坚强、幽默、宽容的东北女性。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皮皮自由的个性。她说:“我不了解母亲。母亲了解我。”“我对母亲的理解,用了她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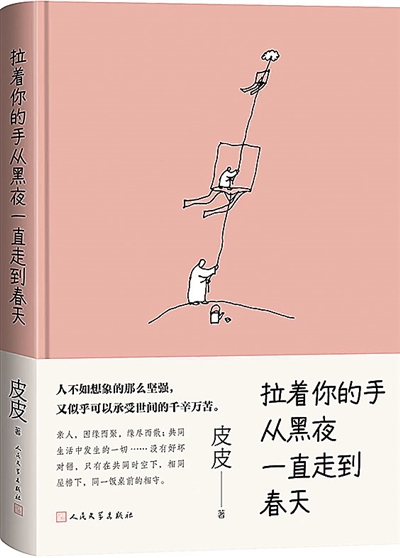
《拉着你的手从黑夜一直走到春天》
皮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01
书中,皮皮用一个有趣的比喻来形容父母:母亲如花,父亲如花土,父亲的存在让母亲的生命盛放。父亲和母亲在多年婚姻中形成的关系模式,似乎是很多家庭的模式,又似乎只此一个。世上所有的婚姻或许都是如此,爱有多深,恨就有多烈。陪伴有多久,厌憎就有多长。反之亦然。相濡以沫和一地鸡毛,从来都相伴相生、褒贬难断。
理解亲人,就是理解生命、理解自己。拉着亲爱之人的手,沿着时光长河漫游,那些我们没说出口的爱,如今都变成了在荒凉世界孤身活下去的勇气和等待春风如约而至的期冀。这本散文集不仅仅是对亲人的爱与纪念,更是写给每一个必经此路的红尘路人。
在真诚又略带幽默的行文中,作家拓展了亲情写作的维度,其间充满对自我与生命的坦诚,她回顾自己与父母从“对抗”走向“接纳”、从“告别”走向“重逢”的心灵旅程。在他们离开后,“我”发现自己对父母最应做到的只有一件事——陪伴。这种理解横跨生死的界河:“他们与我的死别,发生在他们躯体死亡之前。”
什么是世界真正的刻薄与邪恶
如果一定要认识一位当下中国非虚构写作领域的女性,那一定是易小荷。2025年,她的新作《惹作》面世,而人们还沉浸在她上一部作品《盐镇》中女性的生存困境带来的震撼之中。这一次,她的非虚构笔触继续深入中国特定乡土社会的深处,更沉重,也更悲怆。她深入一个偏远村寨一年多,为一个无名、无身份证的普通女性作传,成就了一部兼具文学品格和民族志价值的佳作,这种经历与坚韧令人惊叹。而她也向我们揭示了世界真正的刻薄与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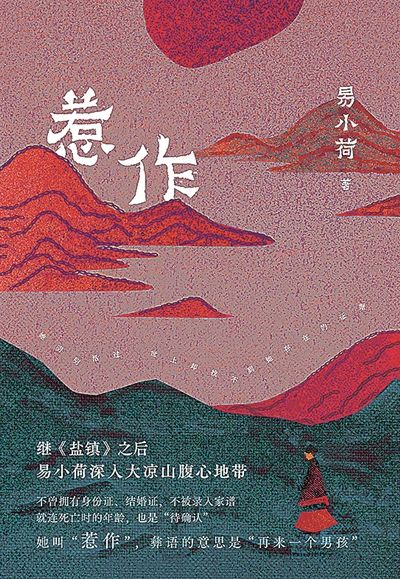
《惹作》
易小荷 著
新经典/文汇出版社2025.01
“惹作”是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女主人公的代称,彝语的意思是“再来一个男孩”。1995年她出生时,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被取名叫“惹作”,相当于汉语里的“招弟”。15岁时,她嫁给了山那边的陌生人,只因为对方的家世与自己的相配。18岁时,她选择喝下百草枯自杀,怀里的女儿只有三个月大。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这只是一个在某年某月喝农药而死的女人。而她短暂又令人唏嘘的一生,仿佛生活在时代与文明之外,又真真切切地存在于21世纪的我们之中。
易小荷深入大凉山腹地,为我们还原了这个几乎“不存在”的女性的一生。她重走了一遍惹作走过的路,去看毕摩做仪式,去她背水的地方,学习收苞谷,学习她爱的民歌,感受一切她的感受。在所有亲人朋友的回忆里,在火塘边的口耳相传中,在毕摩苏尼的吟唱下,重拾一个被遗忘的彝族女性的一生。“那些小径的尽头,都有长久居住其间的人。他们曾经一程又一程地迁徙,越迁越偏远,越迁越高寒,其中一定有许多悲伤凄惨的故事,不过那些事越来越少人记得。但从流传的歌谣中,从不经意的话语中,还是可以想见,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付出过多么悲壮艰辛的努力,才能如同坚韧的荞麦种子一样,落地、发芽、生长,一世世耕种歌哭,直到和这里的高山、红土、瓦房、旷野融为一体。”易小荷所追踪的并不只是某一位女性的命运,而是所有有着相同命运的乡村女性的生命轨迹。她们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刻薄与邪恶的见证。而易小荷的笔,所写的也绝非简单的控诉,而是历史与文明进程中的忠实记录。“当我们重走一遍惹作走过的路,在那条最终通往死亡的小径上,我们感受大凉山的风吹过旷野,瓦岗断壁残垣间玉米叶摩擦的碎响——所有这些,都是惹作的回声。我们终于理解了她为何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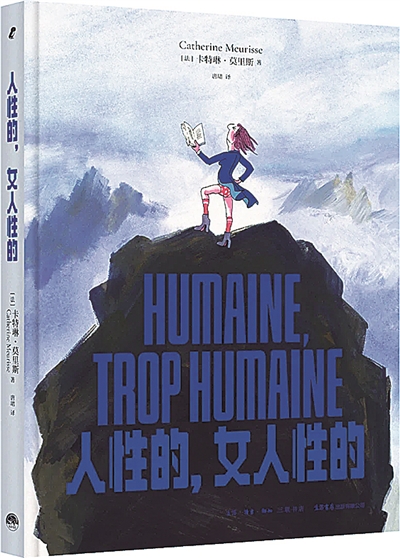
《人性的,女人性的》
(法)卡特琳·莫里斯 著
唐珺 译
三联书店2025.02
■卡特琳·莫里斯为我们画就一张耳熟能详的哲学家地图。作为女性漫画家的她也有机会在此吐槽思想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以严谨和幽默的方式推翻男性神话,勾勒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青岛日报2025年3月7日7版
责任编辑:程雪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