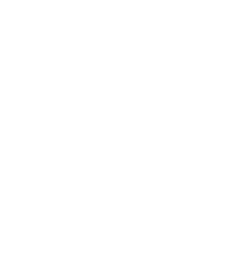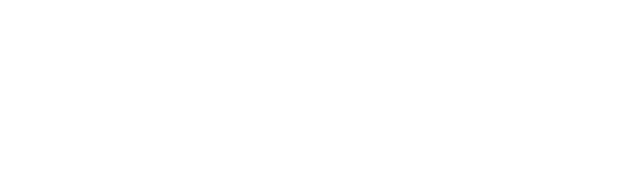编者按
过了腊八就是年,马上到小年了,大年也就不远了。年轻人总觉得没有年味,上了点年纪的人总会念叨着“以前过年那叫热闹啊”。新年来时,最易怀旧,那些最有仪式感的“年味儿”是什么样的呢?来看看四十年前,老日照人乡村的年。
 蒸饽饽
蒸饽饽
馒头,老家叫饽饽,是最高级的食品,不过年,谁家舍得蒸一回饽饽呢?
蒸饽饽有技术含量,泡好面,在炕上发酵一夜,次日和面做饽饽。炕上的被褥掀到一边,露出铺着的稻草,面板、面盆、盖顶等压在稻草上。母亲靠墙跪坐着,两手摁定胀鼓鼓的面团,来回揉搓;父亲则坐在炕下,两手抱着面团反复挤压。面团结实了,揉成柱状,大小均匀一块一块撕下,洒点面粉,像玩陀螺般再揉再团。在双手的来回旋转中,一个个饽饽做好了,摆在盖顶上,等着下锅蒸。
锅里舀了半锅水,水上放屉笼,屉笼上蒙包袱。母亲端来一盖顶饽饽,一个个小心摆开在屉笼上。底下的屉笼摆满了,父亲拿过一个更大的屉笼,刚好压在锅口,铺开包袱,母亲又把另一张盖顶上的饽饽摆上了。等摆好了,父亲抱起靠墙立着的一只旧锅,严丝合缝地反扣在大锅上,母亲把锅沿相接处用包袱垫实,又顺锅沿贴了一圈白菜帮,帮它降温。
烧火了。父亲拿豆秸引燃火,慢慢往里添柴,柴是上山挖的树根,结实耐烧,引燃后不用多添,只需用力拉风箱就行,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帮忙的活儿。刚开始拉风箱时,觉得一来一去蛮有趣,拉久了胳膊就酸痛;风箱呼出来的劲风,把灶里的火吹得旺旺的,把坐在灶口的我烤得热乎乎的。渐渐的,一丝丝气儿开始往上冒,愈来愈多,腾腾热气在屋里弥漫开来,鼻子里闻到了饽饽的香气。母亲擦着手上的面粉从里屋出来,不停地看表,时间差不多了,让我住火。等热气消散,看得清反扣的那只锅了,父亲两手戴上厚厚的皮手套,站到灶台前,深吸一口气,俯身牢牢扒定锅沿,猛地将反扣的锅翻过来,稳稳地靠墙立定。一股热气由锅中腾起,淹没了我们,等热气散去,一大锅白白胖胖的饽饽现在了面前。母亲端来一盆凉水,将手在水中浸浸,轻轻拍了拍一个饽饽,饽饽应手而动,离开屉笼,母亲极快地将它放在一边的盖顶上……
刚蒸出的饽饽又大又软,热乎乎吃下去,菜都不用就。父母也吃了个饱,他们还得熬夜,再蒸一锅。
做豆腐
做豆腐,最累人的是推磨。我们跟母亲一块儿推,从下午推到晚上,好歹把十几斤黄豆磨成浆,剩下的活儿就是母亲的了。她生起火烧豆浆,烧的过程中要不断撇净涌起的泡沫。豆汁烧好了,该点卤了,点卤是个技术活儿,没经验的人决不敢随便动手的。点完囟,眼看着豆浆在锅中渐渐凝结成糊糊状,再将之舀入置于锅上的筐中。筐底铺着包袱,豆浆倒满筐,将包袱四角系起,先轻压几下,再盖上盖顶,上压两块条石,这么压一夜,将豆汁慢慢挤净。第二天早晨,敞开包袱一看,粉白结实的豆腐做成了,豆腐上还留着清晰的盖顶印儿。
母亲一直忙活到下半夜,一开始我们还陪着,等着吃刚出锅的热豆腐。可是等着,等着,眼皮开始上下打架,不知不觉就趴那儿迷糊过去了。再睁开眼时,是睡在了床上,窗外飘来豆渣味,母亲在那儿切豆腐了。
这么多豆腐一时吃不完,母亲将它们大块切好,放进坛里腌着。这坛子豆腐能吃一个正月。
年夜饭
贴完对子,一桌丰盛饭菜摆在了炕桌上,这是母亲和姐姐的功劳。筷子洗净了,烟酒打开了,就等我们入席了。
我们洗净手,大口吸着饭菜的香气,在炕上炕下坐好。年夜饭,父母允许我们吸烟、喝酒,放开肚子吃喝,喝的再多也不会管。酒倒进白瓷盅子里,一口一盅,接连几盅下去,我和哥哥脸上泛红了,耳朵热乎了,口中话多了,口气也大了。抢着给自己倒酒,嫌对方没倒满,话还没说完,一扬脖,又一盅下去了,就连声催着人家“快干”。父亲是滴酒不沾的,母亲一盅酒抿到吃饭,他们都看着我和哥哥笑,催我们多吃菜,别干喝呀……
母亲和姐姐吃过饭后,端来面和馅包饺子,有几个饺子里放了硬币,看明天谁有福,能吃到它们。饺子包完,外边开始传来断断续续的鞭炮声。愈近午夜,鞭炮声愈烈,父亲也拎出一串鞭炮出去放,噼噼啪啪一阵脆响。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旧的一年过去了,新一年开始了。就在鞭炮声中,有人醉了,有人睡了,有人还在看电视。无论醒的睡的醉的,都在憧憬着一个新年……
拜年
睡梦中,被一阵清脆的鞭炮声惊醒,抬头望望窗外,还黑着呢,谁家这么着急?也就睡不着了,亮灯起来,跑到东屋里。父亲已经起来,拿一迭火纸在灶口点了,然后从抽屉中取出盘子,盘子里是瓜子、糖果和香烟;又摸出一挂鞭炮,我和哥哥接过,系在竹竿上,来到院子里。我将竹竿高高举起,哥哥接过父亲点燃的烟卷,一点点地往鞭炮芯上靠,“扑扑扑”,闪烁起了火花,我本能地后退了几步,哥哥也跑开好远,捂起了耳朵。“噼里啪啦”,鞭炮一连串地炸开了,那声音在我们听起来,比别人家响亮的多。
门还关着,等我们捡拾完零落的鞭炮才能敞开,不能让别的孩子抢拾了去。开门,跑进几个气喘吁吁的伙伴,都新衣新鞋,大家汇合到一块儿,挨家挨户拜年了。
先拜本家,紧邻的六爷、隔壁的三伯,还有东头大娘家,都开了大门等着呢。我们人还没进门,先大喊起来:“过年好!”“拜年喽!”大人们乐呵呵答应着,随手抓起一把糖果或瓜子,塞到我们手中,又让座、让喝水,我们哪儿顾得上呢?得赶紧奔下一家去……
村子小,人家少,天色刚亮开,基本都转完了,我们不急不火地往家走,摸摸衣兜,被糖果塞满了,得有多少呢?多数人家给一块,有的人家大方,每人给两块。我们议论着各家的大方与小气,回家把糖果掏出,添入盘子里,赢得母亲一句夸奖:拜的不少啊,都走到了么?走不到,人家会说的。
出来最晚的是老人。他们是吃完水饺,接待完来拜年的晚辈,才到年龄更大、辈份更高的人家走走。到那儿,坐下,慢慢喝茶聊一阵子。聊着聊着天晚了,主人取出盘碗摆在炕桌上,菜肴都是现成的,喝几盅吧。来人并不客气,温了酒,喝起来,一直喝到老伴连声埋怨着找来……
“看故事”
踩高跷,老家叫“耍故事”,看高跷也就是“看故事”了。一家人正在说说笑笑呢,外边忽然传来鼓乐声,夹杂着散乱的脚步,有人喊:耍故事的来喽!一阵阵锣声也由远而近,震动了半个村子。于是都停止说笑,争先恐后冲出门外,往大街上去。
那儿早围了许多人,既有本村的男女老少,也有别村来走亲的,还有跟着高跷队一路赶来的。人占满了半条街,当中圈出一块场地,场地一边停了辆拖拉机,车兜里摆着旱船、高跷等道具,车上车下都是人。二十多个青年男女,脸上都搽了胭脂,胸前飘着彩带,解了绑腿在那儿说话。两三个老头坐在车前,手中持二胡或锣鼓,是奏乐的;其中一个是领队,这会儿正在向小跑来的村干部介绍他们的节目,商量了一阵,选定了几个。
一通锣鼓声起,演员们手忙脚乱地系好高跷,男女各一边,排成队伍,伴着先是急促、后是悠扬的乐曲踩场子。两只旱船在打扮得怪模怪样的老嬷嬷指挥下,围着圈子兜转起来,船中是俊俏的女子,老嬷嬷的闺女;划船的是年轻后生,边划边偷眼瞟那女子,被老嬷嬷发觉了,“啪”的一声,破蒲扇打在脑袋上,后生忙将头缩回去。引得我们一阵大笑。看顾女儿的老嬷嬷,是高跷队中最逗趣的角儿。
人们纷纷往后退,场子越来越大,场地里是无数尖细的高跷跟踩出的坑洼。忽地,乐曲声止,队伍收起,一对男女走至场子中央,拜了年,接着报节目,每年都演的那几个:《小放牛》《箍大缸》等等,大家都能记住词了。演员们刚开始唱,我们也跟着哼哼:
赵州桥是什么人来修?
玉石栏杆什么人留?
什么人骑驴桥上过?
什么人推车压出一道沟来哟……
传说,神话,押韵的腔调,都给人一种悠悠然、又说不出的感觉,自己似乎离开了村子,跟着剧中人去了幽远飘渺之处……
“耍故事”要讨“彩头”的,人家年也不过,亲戚也不走,费心费力地演啊唱啊的,给点“彩头”是应该的。村干部拿来几条烟,或是几十元。这我们倒不关心,我们热心的是他们花花绿绿的扮相,长长短短的唱腔,没了“耍故事”的,没听见锣鼓声响,总觉过年少了什么,不够喜庆似的。(来源:黄海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