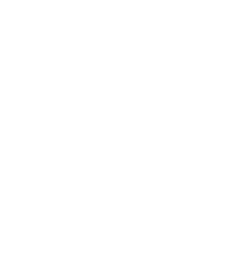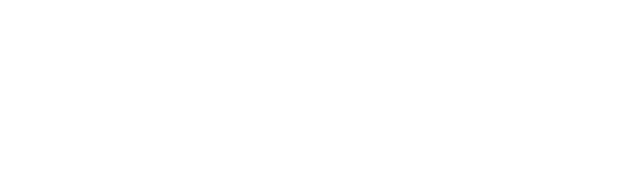青岛日报社/观海新闻9月14日讯 皮达和皮卡,作家曹文轩笔下的这一对活宝兄弟的故事仍在继续。“皮卡兄弟”系列第15本《拖把军团》日前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这本着重讲述孩子成长过程中必备的成长力和同情心的儿童文学新作,也传达了曹文轩一贯的写作理念“幽默的最高境界是智慧”。而曹文轩也在该书正式面世之际特别发声,表示:“我不可以停止对这一形象的书写,我要为中国儿童文学塑造一个广为人知的艺术形象。”
“皮卡兄弟”系列图书是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的校园成长小说代表作。善良、纯真、机智又爱想入非非的皮卡用一个孩子的清纯目光打量着这个世界,经历着对他来讲稀奇古怪的各种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的认识和了解,感受着光明与黑暗,温暖与苍凉,在五味杂陈的成长滋味中慢慢长大。而进入青春期的皮达叛逆、不羁、自我却又时刻护卫着自己的弟弟皮卡。皮达、皮卡兄弟俩在跌跌撞撞中摸索着成长,这些成长包括了身体的、心理的乃至精神的成长。
应该说,皮卡兄弟的故事就是当下中国孩子童年生活、中国家庭亲子关系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是一些小故事,也是一些大故事,是陪伴孩子们成长为“更好的人”的极其珍贵又独一无二的故事。
这也是曹文轩所追寻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境界。他在新书的写作札记中表示:“我的不同情调与风格的作品,看似差别很大,其实懂我创作精髓的,还是会看到它们在题旨、美学上的一致性的。《草房子》也好,《大王书》也好,《皮卡兄弟》系列也好,还是一个文学家族的,就像是一娘所生的几个兄弟,性情各异,但细看,深看,还是一家兄弟。《拖把军团》无论看上去与《草房子》《大王书》有多大的不同,我在写作时的感觉、情绪,却一如既往。”
曹文轩今天接受记者采访,再度重申了他的儿童文学创作观。
观海记者:这次《拖把军团》出版距离上一本皮卡故事新作出版已有6年的时间,是什么原因让您在6年后决定再次创作新的皮卡故事?
答:很多年前,我就知道,我内心不只是有书写《草房子》《青铜葵花》这一类作品的冲动,我还有书写其他情调和风格作品的冲动,并且这些冲动不时地会像狂风中的波浪在心海中扑打和咆哮。我喜欢锐利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但我骨子里一定又驻扎着浪漫主义之魔。后来,我写了《大王书》,这部作品不再是小桥流水、竹篱茅舍,而往气势磅礴、长风万里去了。它的风气令人怀疑是否出自我手。然而,它就是我的心灵之作。记得当年写完,真有一泻千里的感觉。
我写皮卡兄弟的故事。它的情调与风格,既与《草房子》《青铜葵花》大不一样,更与《大王书》迥然不同。我写它时同样感到得心应手,毫无生涩之感。另外一种写作感受,使我感到迷恋。也许,我可能是那种喜欢多种写作路数的写作者。有些作家也许一辈子只写一种情调和风格的作品,他们照样也能成为大家,但我不想这么做,我只想顺其自然,我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想将自己拘囿于一隅。但我也知道这些不同情调与风格的作品,看似差别很大,其实懂我创作精髓的,还是会看到它们在题旨、美学上的一致性,它们的基因是一样的。
《草房子》也好,《大王书》《皮卡兄弟》系列也好,还是一个文学家族的,就像是一娘所生的几个兄弟,性情各异,但细看,深看,还是一家兄弟,它们有许多共同的品质。《拖把军团》无论看上去与《草房子》《大王书》有多大的不同,但我在写作时的感觉、情绪,却一如既往。我已决定,从现在起,我要将以皮卡兄弟为主人公的系列继续写下去,让这一系列成为规模很大的系列。现在,我觉得前几年的中断甚至要结束这一系列的写作的想法是愚蠢的。我不可以停止对这一形象的书写,我要回到这样一种写作语境,为中国儿童文学塑造一个广为人知的艺术形象。我知道,儿童们的认知心理,会倾向于一个形象的不断书写。我要写出既幽默,又能在幽默之后还能留下许多宝贵记忆的作品。我要将我“幽默的最高境界是智慧”的想法付诸实践,写出一个能让现在的孩子喜欢,而当他长大之后再回忆起当年的阅读时,不感到浅薄和害臊——非但不感到浅薄和害臊,还会又有新的感受的作品。也许做不到,但我会竭尽全力去做。
观海记者:皮卡兄弟的故事大部分都是您在2016年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之前创作的,这次的《拖把军团》是获奖之后的创作,写作时会有什么不同。
答:我不想让获奖成为压力,它只能成为动力。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在不停地写,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2017年出版了《蜻蜓眼》,这是一部在我个人写作史上很重要的作品——我坚信这一点,时间将为我证明。后来写了“曹文轩新小说”系列,2020年,因为疫情我被困在了家中,我能做的就是看书写书。《拖把军团》写于2019年年末。在未写之前,我通读了全部的皮卡故事,一是为了找回写这类作品的感觉,二是看看这些作品中是否留下了一些可以发展的线索,三是搞清楚都已经写了什么,以防后面重复。写皮卡故事的心火再次点燃,我回到了六年前,但又和六年前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毕竟已经六年——这六年间,我对文学又有了新的理解,特别是对这一类的作品,更有新的理解。
观海记者:这次《拖把军团》与之前的皮卡兄弟系列比,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大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往后写下去,可能就是这个路数了:一本书只写一个完整的故事,让它们成为一部部长篇小说——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这要比以前那种写几个故事结构一书的方式,显然更具难度。但我很喜欢现在这种方式,我是一个愿意思考结构、经营结构的写作者,我会在结构中获取快乐——特别是那种较大规模的结构。我将其看成是对我能力的考验。那种写作,让我有设计师、工程师的感觉,这种感觉很不错。
观海记者:和《草房子》《青铜葵花》里的家庭相比,《拖把军团》中皮卡的家在您的作品中具有了鲜明的都市中产家庭的特征,这是您的作品中第一次有此突破。
答:从《草房子》开始,我写了不少作品,但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个叫油麻地的地方,一块如同有人在评价福克纳的作品时所说的“邮票大一块”的地方。我关于人生、人性、社会的思考和美学趣味,都落实在这个地方。但大约从2015年出版的《火印》开始,我的目光便开始从油麻地转移,接着就是《蜻蜓眼》,情况就变得越来越明朗了。接下来,我以“曹文轩新小说”命名写了《草鞋湾》,不久前又出版了《寻找一只鸟》。我心态的变化是:我越来越不满足只将目光落定油麻地。我告诉自己:你的身子早就从油麻地走出了,你经历了油麻地以外的一个更加广阔也更加丰富的博大世界;在那里,你经历了不同的生活与人生,这些与你的生命密切相关的经验,是油麻地不能给予的,它们在价值上丝毫也不低于油麻地;你可以不要再一味留恋、流连油麻地了;你到了可以展示油麻地以外的世界的时候了,你到了书写你个人写作史的新篇章的时候,这新篇章的名字叫“出油麻地记”。我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研究者。我发现,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很容易因为自己的作品过分风格化,而导致他的写作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经营。因为批评家和读者往往以“特色”(比如地域特色)的名义,给他鼓励和喜爱,使他在不知不觉之中框定了写作。
我在城市生活的年头是乡村生活的年头的三倍。我觉得我现在写城市与写乡村一样顺手,完全的没有问题。我有不错的关于城市的感觉。写一座城市与写一座村庄,写一条街道与写一条乡村溪流,一样的得心应手。就这么转身了,转身也就转身了——其实我早就转身了,从《根鸟》《大王书》就开始了,但当时没有明确的意识。我觉得一切都在很自然的状态里。
观海记者:可不可以说,《皮卡兄弟》系列后,您的创作开始更加接近于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形式更加丰富,童年特征也更加鲜明。
答: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范型是什么?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我们心中好像有一个儿童文学的“样子”——它比较轻松,比较单纯,比较温柔,它的读者年龄是幼儿、十一二岁以下的儿童,是那样一种用“浅语”写作的文学。但后来我们发现了问题:那些还没有成为“青年”的初中生甚至高中生呢?我们发现了一块广大的没有得到儿童文学厚泽的贫民区。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一度纷纷进军这块贫民区,直到有人开始怀疑:这还是儿童文学吗?但我们即使处在被扣上“成人化”帽子的尴尬处境之中,仍然不顾一切的向上、向上……因此,中国的儿童文学与那些学者们、传统的儿童文学作家所认可的世界儿童文学的范型区别开来了,形成了一道中国的文学特有的风景。我就是其中的一员。但我是“折衷”的,我在想着为高年级小学生、中学生写作时,始终没有忘记那些儿童文学的经典。我在写《草房子》《青铜葵花》这样的作品时,潜意识中,始终有一个儿童文学的“样子”。我不知道我这种选择是否是合理的、明智的。但,后来我在那种“向上、向上”的冲动中慢慢地掉转头了,开始下行——不是那种断崖式的跳水,而是一种顺势而下,于是就有了你所说的”笨笨驴”系列、“萌萌鸟”系列(现在改名为“侠鸟传奇”)、“我的儿子皮卡”系列。但无论是往高处还是往低处,有一点却是始终不能忘怀的:我写的是文学作品。其实,我一旦进入写作状态,是不怎么想到读者是谁的。(青报全媒体记者 李魏)
责任编辑:单蓓蓓